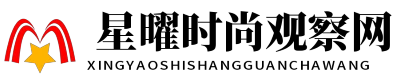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影大师做客电影学堂,以对谈的形式分享个人电影理念和创作心得,畅谈光影艺术的魅力。
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影大师做客电影学堂,以对谈的形式分享个人电影理念和创作心得,畅谈光影艺术的魅力。从2017年的第20届至2021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,先后已有克里斯蒂安·蒙吉、布里兰特·曼多萨、努里·比格·锡兰、贾樟柯、是枝裕和、丹尼斯·维伦纽瓦、甄子丹等中外电影大师走进SIFF电影学堂,进行了16堂高水准的讲授与对话。
“SIFF电影学堂精粹”带你回顾电影学堂的对谈实况,感知电影大师的个体经验与时代关照,领略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,抵达更广阔的光影世界。
以下为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丹尼斯·维伦纽瓦导演大师班实录:

关于丹尼斯•维伦纽瓦
丹尼斯•维伦纽瓦(Denis Villeneuve)是法裔加拿大电影人,导演作品包括《沙丘》《银翼杀手2049》《降临》《边境杀手》《焦土之城》等,曾担任2018年戛纳电影节评委。大师班举办之时,维伦纽瓦正在进行《沙丘》后期制作。在最新公布的奥斯卡入围名单中,该片获得最佳影片等10项提名。
丹尼斯•维伦纽瓦导演大师班集锦
时间:2020年8月1日(周六)20:00-21:00
嘉宾:丹尼斯·维伦纽瓦加拿大导演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朋友们,大家好。我是丹尼斯·维伦纽瓦,法裔加拿大电影人。今天我以大师班的形式和大家见面。我非常希望和大家真的面对面,但今年(2020年)情况特殊,这一愿望目前无法实现。感谢大家的理解。就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线上的方式吧。我的同事塔尼娅和我在一起,她来负责将上影节拟好的问题向我提问,希望大家会觉得值得一看。
提问:我们现在在蒙特利尔,你和大家一样远程工作,你在制作《沙丘》,目前为止疫情对制作的过程有哪些影响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是的,我目前正在制作电影《沙丘》。我们的拍摄接近完成,电影也接近完成状态。在制作《沙丘》这部电影的时候,我们采取了一些不寻常的方式:在完成了主要拍摄部分后,先把那部分剪辑出来。原本计划是以后再继续拍摄,因为我想调整电影。而当时我有充足的时间。那时候我没有预计到疫情的爆发。当我们正要重返拍摄的时候,疫情袭击了北美。疫情完全扰乱了我的计划,我必须全力冲刺才能按时完成这部电影。我们刚被允许回去补拍,我几周后就要出发,但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应该完成的。这也意味着,我必须远程参与电影的一些部分,比如特效、剪辑。
我在蒙特利尔,制作团队都在洛杉矶。作为导演,现在很多工作可以通过科技远程完成。远程指导特效是比较容易实现的,我也比较得心应手。但这一次让我意识到,远程指导剪辑不是容易实现的,我本以为是可行的。我和剪辑师们相隔千里,通过电脑共享协作,但我意识到剪辑就像和别人一起玩音乐,你们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。人与人之间在同一空间的即时反馈很重要。我非常怀念和剪辑师一起工作的日子。从艺术创作的角度,无法和我的剪辑师在同一个地点工作真的很痛苦。另一个原因是,剪辑师不仅仅负责电影的剪辑,也像心理医生能缓解我的焦虑和恐惧,分享我的喜悦。如果将来类似的情况再出现,我绝对要确保剪辑师就在身边。对我来说,剪辑是电影制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,可能是最重要的环节。这阶段你以某种方式对影片进行重塑。在你创作电影的过程中,从剧本到拍摄,再到剪辑,你都在一步步完善这个故事。但对于剪辑来说,就像你面前已经有了完整的字母表,所有的语言和画面都已经备好,你不用担心阳光、刮风、或者演员的身体状况,所有的元素都摆在这里。这能极度激发创意,这个过程十分神奇。你可以在剪辑室里创造出恐惧、喜悦、压力,可能这也是为什么,这一次远程和剪辑师工作,让我有阴影了。
提问:你再一次和作曲家汉斯·季默合作,他也曾提到创作中的亲密程度很重要,但现在你们也是在远程沟通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作曲也是一样的性质。我和汉斯·季默一起在做这部电影时,因为不能在一起工作,他也很崩溃。是真的。就像你欣赏音乐或演唱的时候,你能够感受到身体语言,你可以感受到身旁那个人的能量,你明白有些事情是无法说谎的。这不仅仅是智力的过程,更像是直觉,一种感知力。在同一空间,你能真实体会到电影和音乐给人的感受,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当电影和剪辑快要完成的时候,我会邀请一些观众观看,和他们坐在一起,这个过程你能学到很多。你可以直接看到电影的感染力,你也能看到不足,你必须保持谦逊,虽然有时候自尊心会受伤,但你必须经历这个过程。这能让你学到很多,而这些是无法通过远程来感受的。
提问:但在视觉特效方面,远程工作的效果却还不错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是的。这一次很关键,我和大师级别的波林·格里伯特一起工作,我们有着相似的对事物的感知。特效的过程与剪辑不同。如果说剪辑更像一起玩音乐的话,特效则是一个对所看所见进行反馈的过程。观看、反馈、修改、再等一两周看到结果的过程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清晰的头脑,保持一定距离,有助于得到更自然的反馈。你需要专业的设备支持。目前为止,特效部分进行得非常好。
在《沙丘》项目中,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特效团队,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鼓舞着我。我和特效团队几乎每天都开会,通过网络进行一小时的会议。当我在家里看到他们分享过来的画面,支撑着我度过疫情阶段,眼见着特效慢慢完成,工作慢慢完善。我们的团队其实分布在世界各地。特效团队成员有的在温哥华、洛杉矶、蒙特利尔,也有的在欧洲、亚洲,世界各地都有。所有人在家的努力成果,最后汇集到我这里。

提问:我们来细聊一下《沙丘》的世界。这是对弗兰克·赫伯特1965年小说的改编。你是如何执导这部电影?又如何看待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的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初读《沙丘》这部小说,那时我大概13、14岁的时候。坦白来说,我是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这本书的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封面的时候,我还是一个深爱读书的青年。我喜欢阅读,并从中寻找各种新鲜事物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,我开始展露出对科学的擅长,我开始对科幻小说越来越好奇,越来越讶异和惊叹,特别是《星球大战》。你知道,1977年《星球大战》的出现让我一下子成了它的目标观众。《星球大战》有很多元素取自《沙丘》。众所周知,乔治·卢卡斯也是《沙丘》的书迷,所以能轻松地从中汲取灵感,吸取一些书中的元素,一些神话体系,一些世界观架构和故事推动力。
《沙丘》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小说。第一次见它时就有这种感觉。我看到这本漂亮的书,封面上有一个蓝眼睛的男人。我现在还保留着那本书,仍然记得当时被它的封面所惊艳。我还记得我翻看了书的背面,它的确吸引了我,我深深沉浸其中,读完了这系列的全部小说。这是一个传奇,一共几本书,用某种方式描绘了世界的复杂性,美丽又丰富的文化。一个男孩离开家乡,不得不在一个新的现实中适应,在新的文化中生存,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去拥抱新的文化,在那个环境里生存。这让当时的我深受感动,我那时也是一个年轻男孩。同时我也认为这本书探讨了、经济,我们如何解决自然资源问题,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破坏。作为一个孩子,对我来说,这是一本复杂又充满力量的小说。通过一个强大又简单的普世故事,同时探讨复杂的议题。老实讲,它成了我那时最喜欢的书。我深爱着它,并且在我以后的生命中也将会持续这种热爱,它就像一个古老的梦。我曾对自己说,有一天我要把它搬上银幕。
我记得我很激动,当大卫·林奇将它改编成电影的时候,我非常激动,我一直期待着看到它。事实上,当我看到电影中有很多我深爱的元素后,我就觉得大卫·林奇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,他是一位大师,我非常敬重他。但同时他的改编中也有另一些让我感到疏离的部分。那是他眼中《沙丘》的样子。我明白了不止一个《沙丘》的含义。有一种情绪总是触动着我,我对自己说:“也许是将来的某一天吧,我会拍《沙丘》”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拍电影,但主要是加拿大的一些低成本电影,科幻片对我来说遥不可及。来到好莱坞之后,我开始拍摄更高成本的好莱坞。人们不停地问我:“你的终极梦想是拍什么样的电影?”,或者“你想要做什么?”,我一直说我想拍科幻片,我想拍《沙丘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传奇影业的玛丽·帕伦特和凯尔·柏伊特拿到了版权。他们一拿到版权给我打了电话,这可能是我开过最短的一次会议。我们只是说了句:“我们要一起拍《沙丘》吗?”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从一开始,我们就对《沙丘》原著以及这个故事该如何被讲述,有着同样的感触。在项目中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合作。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目前为止经历过的最大挑战。

《沙丘》剧照
提问:既然《沙丘》的影响力如此巨大,那么它对你之前的电影也有过什么影响吗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我会说,它加强了我对无尽沙漠的渴望。对于保罗来说,关于沙漠,那些空旷景象的冲击,寂寞的冲击,都成为了他内化的、潜意识的旅程。这意味着当人物走向沙漠更深处时,我们也走到了他内心更深处。这是我从书中感受到的,自然景观对人类灵魂的影响。我在以前的电影创作中也有所尝试。我最初的影片,一男一女在沙漠中爱上了对方。更准确地说,是一段发生在沙漠中以失败告终的爱情。这不是巧合,而是我想要探究景观如何影响人类,自然如何唤醒内在情感。
你看我早期在约旦拍摄的电影《焦土之城》中也出现了沙丘。这部电影改编自瓦吉·穆阿瓦德的作品,我在其中展现了一部分沙漠,是在约旦取景拍摄的。我记得是因为我在约旦游走观察——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陌生的中东国家,这个不存在的国家却代表了黎巴嫩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部分。我经常说,我走遍了约旦,探索了约旦沙漠的每个角落。我记得我对自己说,这对《焦土之城》来说不够适合,但对《沙丘》来说却显现着近乎疯狂的美。如果我要拍《沙丘》的话,一定会回来这里取景。我确实这样做了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《沙丘》已经存在于我的作品中好久了。
提问: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演员的选择和拍戏时的合作。你是如何挑选演员的?更看重演员的哪些特质?可以结合《沙丘》这部电影,也可以谈论一下你的其他电影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选择演员非常非常困难,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过程,但同时又是一个让你兴奋的时刻,但同时又很紧张。你需要一个演员化身成这个角色,赋予角色语言和生命。更重要的是,你需要找到你的缪斯,你需要找到能激发你灵感的人,能激发你创造力的人,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。就《沙丘》而言,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但非常有趣。
让我非常开心的是,我大多数的“第一选择”的演员都会被项目本身的魅力吸引,并答应参与这个项目。对于《沙丘》这部传奇一般的经典来说,说服人们一起加入并不是难事。刚开始提莫西·查拉梅就是我的第一选择,我心中的保罗·厄崔迪就是提莫西。和提莫西见面后我们立刻达成共识要一起合作。说服提莫西并不难,选择提莫西有几个理由:首先他是一个现象级的演员,他极具深度,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。保罗·厄崔迪年轻的身体中住着老练的灵魂,提莫西也是如此,看起来比他的真实年龄还要年轻。有时我看着镜头中的他 ,感觉他只有15岁,但实际上他大概有23岁左右了,这真的很令人惊讶。他深邃而饱经沉淀的眼神也起到了很大帮助。而且他已有超越年纪的成熟,能够制造这种年龄的反差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他的一些特质也会让我想起过去经典时代的好莱坞电影明星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电影明星,疯狂散发着个人魅力。你将镜头对准提莫西,会感受到魅力爆发的瞬间,就像摄像机突然被他吸引住一样,非常有魅力。这也是保罗需要具备的特质。保罗是一个需要在某个时刻领导和激励别人的年轻人,成为一个领袖,他需要这种魅力。而提莫西有这种魅力,从某种意义上讲,他就像一个摇滚巨星一样。我需要那种魅力,我需要他可以刻画出保罗不同层次的性格。
现在我可以将(《沙丘》)所有演员都细数一遍,但这可能要花上3个小时,因为这个项目中让我有机会和一群现象级的演员们一起工作,而每一位的选择都有其特定的原因。例如我选择杰森·莫玛是因为他对待冒险放荡不羁的态度、他在银幕上的优雅、镜头中不可思议的笑容,都散发着致命的魅力。他打斗的时候像是一个芭蕾舞者。作为银河系最好的战士之一,需要呈现一种骑士般的高贵、勇猛,同时又不失幽默,他是这个英雄的不二人选。同时我也有幸和乔什·布洛林一起合作。他是我之前就合作过的演员,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细数每位演员,这个话题能聊很久。我曾经和乔什·布洛林合作过,我一直想和他再度合作,因为他是我喜爱的演员,也是我喜爱的诗人。他在片中扮演哥尼·哈莱克,一个诗人、战士,有时略显颓废。当乔什出现在银幕上时,你会爱上他的角色。尽管他的角色有时不修边幅,这正是我需要的。作为保罗最好的朋友,他也需要这种气质。我希望能和乔什·布洛林一直保持合作,他真的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演员。我也很早就想和奥斯卡·伊萨克一起工作了。奥斯卡完全符合小说对雷托公爵的描述。他也是当今最的男演员之一,我一直在寻找与他合作的机会,最后他同意饰演公爵。还有斯蒂芬·亨德森,他的角色可以用“人类计算机”来形容。《沙丘》世界中不再出现计算机,人类决定把机器弃之一旁,使用大脑工作。其实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斯蒂芬正好是我想寻找的,一个眼睛里充满智慧,同时又看起来像泰迪熊的演员。我想要观众在看到斯蒂芬的瞬间,就自发地爱上他,想要拥抱他。在确定完提莫西参演之后,我们紧接着邀请到的是丽贝卡·弗格森。选择她的原因也很多,她是一名伟大的艺术家。我认为她能胜任杰西卡夫人这个复杂的角色,这个人物层次很丰富。还有夏洛特·兰普林,这位长久以来我渴望合作的女演员,对我来说是一个传奇,我喜欢她有25年了。斯特兰·斯卡斯加德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。我的老朋友大卫·达斯玛奇连,我希望我所有电影都有他的身影,因为我很享受和他一起创造人物的时刻。同样还有戴夫·巴蒂斯塔,我和戴夫在《银翼杀手2049》中有过合作,没有比他更适合演“野兽拉班”的人了。戴夫非常可爱,但他长得很凶很吓人,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,他是一个能感动我的演员。对了,还有震·张,中文里应该叫“张震”。我从90年代王家卫的电影就开始关注他,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演员之一。我在很多电影里看到过他,被他自然的表演深深打动,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之一。

演员张震——《沙丘》
提问:和这些演员们一起拍摄,你感觉怎么样,或者说你和演员是怎么合作的?你如何给意见、如何给他们导戏?你在片场一般如何指导演员们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我认为有两件事非常重要。首先是准备要足。对我来说,所有的智识上的工作都要在拍摄之前完成。我喜欢在一个完美场景下工作。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晰,对话也好,场景也好,所有智识层面的讨论,都要在准备阶段完成。所以在前期的时候,这时候我会和演员们沟通,和他们聊角色和影片情节逻辑,及时调整,我不怕做出调整。如果某位演员对于影片对白有更好的想法,因为有时候对白容易写得过满,编剧在撰写剧本时是想从文字到大银幕的过程,但当你看到演员的眼神,就知道可能有另一个表达方式。这在我和演员们的沟通中时有发生。当这部分智识工作完成之后,我在片场就更专注于场景的视觉化,专注于情感,引导演员经历情感变化。这个指导过程不要太理性化,因为我很注重情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最终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人的变化过程,以及那个场景对人的影响。大部分时候,在我个人看来,当你在那个场景里时,想法就会随之出现。因为它本来就被安置在那个场景里。
我的工作方式是,尽量多给演员空间。希望是如此。首先我会确认,最大程度在真实的场景里进行拍摄,而非特效场景里。我相信那影响着演员的创作过程。演员们能知道,这里有一扇门,这里有沙发、房间的色彩布局,这里有灯光、也有植物,这些都会激发创意和想象。它能在演员内心产生张力,制造压力,也可能是其反面——自由。而我作为导演,最重要的是观察与聆听。开始阶段,我需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,聆听他们,看他们从直觉里带来的东西。有时候他们也会有不太好的创意,我会忽略这些。有时他们的创意比我的要好,我要及时地去倾听。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平衡。有些演员的直觉比其他人要好,这些都很自然。这是灵感,而不是科学,需要你有敏锐的感知力。一个好导演同时也是一个好的倾听者。我导演的经历越多,就越发觉得,开始阶段,导演需要允许有一定自由的限度,让一些诗意的想法有机会进来。我对此始终坚信,我说的不是即兴创作,而是给创作者空间。
提问:在你成为导演的职业道路上,有没有对你影响颇深的电影人?他们的电影作品是否也影响了你自己的风格、定位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有很多电影人对我的影响颇深,他们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中一位,直到今天依旧对我非常重要的,无疑是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。我来自一个小镇,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大部分是美国电影。而有一类电影和其他电影截然不同,这类优秀电影都和一个名字有关,带着这个名字的电影就意味着质量保证。慢慢大家就意识到这一点。那个人做着一种工作,那个工作就是导演。而他的名字就是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。后来我开始看一些幕后花絮,开始明白这个工作的重要和意义。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 ,我最喜欢之一是《第三类接触》。而电影的主演弗朗索瓦·特吕弗是一名法国导演,所以这部外星人电影也让我发现了“法国新浪潮”。弗朗索瓦·特吕弗的作品中有对人类之间的爱的描述,他的描述如此深刻。我非常喜欢他深具同情心。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无疑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导演之一,他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导演。他创造了无数经典场景,与演员们一同完成调度,摄影技巧同样无与伦比,直到今天我也时常会重温他的作品,非常令人钦佩。在弗朗索瓦·特吕弗之后,我又知道了戈达尔。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智慧、乐趣和激励人的力量,激励观众做一个发声者。我当时是个自大的年轻人,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套很管用。
就这样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导演,斯坦利·库布里克也是对我影响非常深厚的导演。毋庸置疑,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演之一。在我探索电影的过程中,如果说到在精确与纯粹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实现平衡,库布里克达到了让人难以企及的境地。还有英格玛·伯格曼,对我产生了强烈的美学冲击,他深切地碰触人类的灵魂,到达人类意识的最深处,诚实地展现人性的真实。还有很多导演也对我产生深刻影响。接下来必须要说雷德利·斯科特。《银翼杀手》给我的美学冲击很大。在法语中我们称其为“视觉艺术家”(plasticien)。他能够建立起一个自己的视觉世界。还有无数当代导演是我非常崇拜的。先不提其他的法国导演,比如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:雅克·欧迪亚,还有欧格斯·兰斯莫斯。克里斯托弗·诺兰在我心中也是无可超越的存在。绝大多数导演做不到的事情,他却可以。在操作巨大体量的项目的同时,还能保持自己的个人风格。我可以说是诺兰的头号粉丝了。在众多导演中还有一位,是每当我拿起摄影机就会想到的。实际上是两位:皮埃尔·佩罗和米歇尔·布洛尔特,两位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导演。他们在六七十年代拍摄的纪录片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和他们的作品没什么关联性。确实我们的作品很不相似。但时至今日我和他们一样,在自然面前感受谦卑,愿意去拥抱自然,并且从中汲取诗意。他们的影片中有这样一种情感,那是我至今仍在努力保持的情感。即使我如今在好莱坞工作,我仍感觉两位艺术大师离我很近。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我现在说的,因为他们不喜欢好莱坞,他们讨厌好莱坞,而且我不觉得他们会喜欢我的电影,但我深深敬仰二位,他们对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我想再补充一下,很多人都会问我哪些电影人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?我总是忘记真正的答案,那就是摄影大师们。在这里我想提两位摄影师。第一位是彼时很年轻的安德烈·图尔平。我最开始与他合作时,他还是一位年轻的摄影师。他捕捉真实的精准度极高。当然还有罗杰·迪金斯。当聊到作为一名导演最喜爱的电影人时,一定要提到迪金斯。他是位艺术家,以对光影的掌控闻名。但对我来说却不止如此,他确实擅长利用光影进行摄影,但在叙事方面他也非常了不起。我们一起合作拍摄了三部电影,我能在我们的合作中收获自我陶醉的愉悦。我就是很爱他,他的每一个镜头对我来说都是一堂电影课,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莫名相似。我用了“莫名”这个词,因为对我来说他是个摄影大师,甚至是摄影之神。就算我们已经是亲密的朋友,我还是对他怀有崇拜之情。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相近,因此当我们一起合作时一切都得心应手,无论是拍摄镜头还是布光等等。因为和大师一起工作,我还有一种在学校上课学习的愉快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想再和他合作一次的原因。关于电影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,与罗杰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荣幸之至。

维伦纽瓦与迪金斯在片场
提问:实际上迪金斯曾经说,您的电影是那种——在孩童时代促使他想进入电影行业的作品。两位的关系似乎对你们彼此都有滋养的作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跨越不同的作品,这种合作有什么变化吗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当我和迪金斯合作第一部长片时,我不得不遏制自己作为他粉丝的那一面,而要接受自己作为导演,需要给他提供指示的事实。刚开始的几天,我感到很不自在,也很尴尬。我在生活中通常不会轻易地钦佩某人,但总有一些导演或电影人,在他们面前我会非常羞涩。面对迪金斯,我的钦佩更加难以言表。在合作完第一部影片后,我们成为了亲密的好朋友,之后的合作也轻松了许多。罗杰·迪金斯对他人和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,他必须确保每一个镜头都无可挑剔,于是压力也随之而来,有时他会因为压力而稍显急躁。我曾对他在片场的脾气变化印象深刻,不过现在我已经完全习惯,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舒服。《银翼杀手2049》让我们的合作更加深入,我们一起探讨该用什么样的电影语言呈现。当时时间紧迫,我无法独自完成,便邀请迪金斯一起帮我制作整部影片的故事板,那也是迄今为止我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时刻。我和迪金斯,还有故事板艺术家以及詹姆斯一起坐在酒店房间里制作故事板。就像是和别人一起做梦一样,能够与他合作是我的荣幸,随着合作进行得更多、更深,我们越来越习惯听取对方的意见。很多时候我们无需多言,只需看着对方,通过直觉就能了解彼此的想法。这是一种很纯粹的情谊。
提问:还记得对于一部想拍的电影,你脑海中第一次出现它画面的时候吗?能否描绘一部电影在你脑海中诞生的过程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那么我就跟我的中国朋友们聊一聊我以前从未透露过的秘密吧,这件事说来有几分尴尬。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在脑海里导演电影了,这是我应对恐惧和焦虑的办法。因为小时候对世界感到害怕,每当我要睡觉的时候,唯一能够睡着的方法,就是在脑海中设计一个又一个故事,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世界。一晚一晚的故事就像电影的情节,帮我对抗焦虑,也让我与这个世界真正建立起联系。我从童年起就开始写作,一开始我以为我会成为作家,但我可能天赋不足。当我尝试导演的工作之后,就越来越痴迷这种通过摄影机讲故事的方式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摄影机,但好在我有个朋友擅长画画,我们配合得不错,我来讲故事、他来画,创造我们自己的世界。早期的我通过这种方式,试着去理解周围的世界,有时候是逃离。这可能就是我开始拍电影的契机。抱歉我忘了说,我和我的朋友尼古拉,在我们十二三岁的时候,就开始为《沙丘》制作故事板了。那时我读这本书读得津津有味,便一起开始制作。我现在还有很多当时画的保罗·厄崔迪,还有沙虫。可以说当我还是孩子时,就开始梦想着将《沙丘》做成电影了。
提问:就像我刚刚说的,你很擅长在电影中利用观众对不确定性的心理,制造悬念。能否谈谈为了实现这种效果,通常采取的视听手段?例如:调色、美术、声音、剪辑等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这是关于制造紧张感的问题。每当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时,我通常会回答:这经常是凭着直觉实现的。这样的答案有点无聊,所以这次我会尽量回答得更详尽一些。制造紧张感的最重要元素之一,是让银幕里、影像里的东西具有真实感,从而使观众从潜意识的角度,能与之建立联系。可以是光,可以是植物,也可以是让这个镜头像梦境一样的东西,只要其中存在真实性。用光,就是电影制造真实感的强有力的工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要尽可能呈现多的……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喜爱罗杰·迪金斯的摄影。他的摄影理念就是把镜头里的东西拍得越自然越好。这样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信号,“你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真实的”。
然后你需要引导观众,让他们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看不到的,例如他们的所在,或者恐惧的所在。这时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展现它,给出一些暗示、声音,或者镜头运动产生的压力感,来预示某些事情将会发生、或者不会发生。然后就像炉子上的锅子,你开锅、等待水的沸腾,过了一段时间水会变得足够热,马上要沸腾了,你必须在这里切掉,这是紧张感达到顶峰的时刻。对我来说,一切都要从与自然和时间的关系着手,通过不在场的事物营造紧张感,这是靠留白制造紧张感的诗意所在。目前为止,表达紧张最佳的音乐,永远都是寂静。当你能够通过留白和寂静表现紧张感时,其效果会是很震撼的。

《沙丘》剧照
提问:在您1998年拍摄的长片作《8月32日》结尾处,主人公从魁北克飞往美国。今天看来,似乎也映射了您的导演生涯,您也是最先在魁北克,而后到美国继续拍电影。在这过程中,您拍电影的方式和态度是否发生过明显变化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确实有变化。在一开始的时候,我更痴迷于镜头运动,我有强烈的掌控欲。我在拍第一部电影时非常傲慢,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,去创造一种身份标志。拍了两部电影后,我意识到我失败了。我决定换一种方式看待事物,试着不去证明“我”的存在,换一种方式去表达,努力更谦逊地处理我的主题。由我去服务故事,而不是故事来服务我。我将自我意识摆正,因为热爱电影而去拍摄电影,而不是为了证明我存在,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改变。我还想说的是,我与演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和演员沟通的时候会有点不知所措,很多导演都有类似经历,觉得演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“物种”,这种感觉很正常。但我和演员合作得越多,就越感到舒服自在。我越来越成为一名好导演,去倾听演员的想法,并且更好得掌控工作,拥抱那些自己还没有答案的想法。我现在做得还不错,即使不知道正确答案,也能很自如。作为导演,常常要回答上百个问题。我现在觉得,如果用法语来表达是“自我原谅”,对自己友善,静待花开,即使有500个人等着你,即使太阳就快落山,火正在燃烧,你也要耐心等着花开。花终将绽放,我们必须保持耐心。因此你必须离开焦虑圈,然后再回归创作。这些是我多年来学到的东西,当然我还学到了很多技术上的东西。
提问:《囚徒》和《边境杀手》是您早期的美国电影作品,此后您便投身科幻片,从《降临》、《银翼杀手2049》到《沙丘》。很多人认为这是非常巨大的转变。但实际上您常说,这和您年轻时的热情是一脉相承的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是的。经常有人问我,你现在怎么开始拍科幻片了?你为什么进入这个领域?但我想说,我不是“去到”那个领域,而是“重返”那个领域。我爱科幻,我从一开始就梦想着拍科幻片。我认为要想拍出优秀的科幻片,必须掌握很多要素。对那时的我来说,可能是一种非常困难的类型。所以为了拍好科幻片,我必须在拍摄其他题材的过程中改进和优化拍电影的技艺,在现实中耕耘,才能离梦想更近。我现在能够执导科幻片的另一个原因是:我的预算变多了,也有了足够的经验指导,能够指导更大的工作团队,掌控更复杂庞大的视效。我不可能把《沙丘》作为我的作,如果那么做的话,我现在已经玩儿完了。
提问:您之前提到过,对您而言重要的是这些科幻场景要在真实环境中拍摄,而不是绿幕前。当今技术发展迅速,您如何看待自己与视效的关系呢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现在电脑是非常强大的工具,能制造很宏大的场景,甚至创造一个世界。当然这是我们之前无法做到的。但在过去,导演和视觉艺术家都是大师,他们能运用非常复杂的技术来创造事物。如今利用电脑,会比之前容易一万倍。因此,可以很肯定,我们现在有更大的灵活性。但在我个人看来,存在的危险是,归根结底,电影的灵魂是语言和演员,要让电影拍摄得到最好效果,你需要去激发演员。而要激发演员,我认为大量的“真实”元素很重要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有时不得不在虚拟环境里进行拍摄,对我来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最终真实的效果,是很困难的。因为我不认为创意能够凭空突然冒出来。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,我会对一张被照亮的桌子有感觉,我对房间里椅子的位置有感觉,我对演员是不是以某种特定姿势和角度朝着一扇窗户走过去有感觉。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有一扇窗户,窗外也得有东西,这就像你在为创造力和想象力储备食粮。包括站在绿幕前也一样,你需要在场感。作为一个导演我永远会为在拍摄中有更多真实而努力,拍《沙丘》的时候也尽可能在真实的场景中拍摄。我们搭建了很多非常宏大的场景,我们需要借助这些来思考。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世界,创造一个新的星球,那我们就需要用储备“好的粮食”去创造,我认为这些真实的环境布景很有帮助。当然电脑可以帮助我们完善,使这个世界看上去更大,让东西飞起来,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完成得更完美。但是围绕演员的核心元素则需要是真实的。
提问:作为一个导演,同时也是影迷,在您看来,是什么构成了一部好电影?换句话说,你认为一部好电影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什么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诗意。我认为,归根结底,观众为什么要去看电影?是因为要在影像的诗意中找到感动。当你与别人交谈时,偶尔提到某部电影的名字,你的脑海里会自发地出现一些场景。那些因为某种原因深深印刻下来的场景,会触动你的内心深处,它们有着深刻的含义。这些含义是制作团队在拍摄和打光时就精心策划的。这些设计元素创造了一种无形的含义,它不可言喻、不可见,这就是诗意,这就是电影诗意的美。作为一名电影人,你要在电影中创造尽可能多的这样的场景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
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影大师做客电影学堂,以对谈的形式分享个人电影理念和创作心得,畅谈光影艺术的魅力。从2017年的第20届至2021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,先后已有克里斯蒂安·蒙吉、布里兰特·曼多萨、努里·比格·锡兰、贾樟柯、是枝裕和、丹尼斯·维伦纽瓦、甄子丹等中外电影大师走进SIFF电影学堂,进行了16堂高水准的讲授与对话。
“SIFF电影学堂精粹”带你回顾电影学堂的对谈实况,感知电影大师的个体经验与时代关照,领略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,抵达更广阔的光影世界。
以下为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丹尼斯·维伦纽瓦导演大师班实录:

关于丹尼斯•维伦纽瓦
丹尼斯•维伦纽瓦(Denis Villeneuve)是法裔加拿大电影人,导演作品包括《沙丘》《银翼杀手2049》《降临》《边境杀手》《焦土之城》等,曾担任2018年戛纳电影节评委。大师班举办之时,维伦纽瓦正在进行《沙丘》后期制作。在最新公布的奥斯卡入围名单中,该片获得最佳影片等10项提名。
丹尼斯•维伦纽瓦导演大师班集锦
时间:2020年8月1日(周六)20:00-21:00
嘉宾:丹尼斯·维伦纽瓦加拿大导演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朋友们,大家好。我是丹尼斯·维伦纽瓦,法裔加拿大电影人。今天我以大师班的形式和大家见面。我非常希望和大家真的面对面,但今年(2020年)情况特殊,这一愿望目前无法实现。感谢大家的理解。就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线上的方式吧。我的同事塔尼娅和我在一起,她来负责将上影节拟好的问题向我提问,希望大家会觉得值得一看。
提问:我们现在在蒙特利尔,你和大家一样远程工作,你在制作《沙丘》,目前为止疫情对制作的过程有哪些影响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是的,我目前正在制作电影《沙丘》。我们的拍摄接近完成,电影也接近完成状态。在制作《沙丘》这部电影的时候,我们采取了一些不寻常的方式:在完成了主要拍摄部分后,先把那部分剪辑出来。原本计划是以后再继续拍摄,因为我想调整电影。而当时我有充足的时间。那时候我没有预计到疫情的爆发。当我们正要重返拍摄的时候,疫情袭击了北美。疫情完全扰乱了我的计划,我必须全力冲刺才能按时完成这部电影。我们刚被允许回去补拍,我几周后就要出发,但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应该完成的。这也意味着,我必须远程参与电影的一些部分,比如特效、剪辑。
我在蒙特利尔,制作团队都在洛杉矶。作为导演,现在很多工作可以通过科技远程完成。远程指导特效是比较容易实现的,我也比较得心应手。但这一次让我意识到,远程指导剪辑不是容易实现的,我本以为是可行的。我和剪辑师们相隔千里,通过电脑共享协作,但我意识到剪辑就像和别人一起玩音乐,你们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。人与人之间在同一空间的即时反馈很重要。我非常怀念和剪辑师一起工作的日子。从艺术创作的角度,无法和我的剪辑师在同一个地点工作真的很痛苦。另一个原因是,剪辑师不仅仅负责电影的剪辑,也像心理医生能缓解我的焦虑和恐惧,分享我的喜悦。如果将来类似的情况再出现,我绝对要确保剪辑师就在身边。对我来说,剪辑是电影制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,可能是最重要的环节。这阶段你以某种方式对影片进行重塑。在你创作电影的过程中,从剧本到拍摄,再到剪辑,你都在一步步完善这个故事。但对于剪辑来说,就像你面前已经有了完整的字母表,所有的语言和画面都已经备好,你不用担心阳光、刮风、或者演员的身体状况,所有的元素都摆在这里。这能极度激发创意,这个过程十分神奇。你可以在剪辑室里创造出恐惧、喜悦、压力,可能这也是为什么,这一次远程和剪辑师工作,让我有阴影了。
提问:你再一次和作曲家汉斯·季默合作,他也曾提到创作中的亲密程度很重要,但现在你们也是在远程沟通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作曲也是一样的性质。我和汉斯·季默一起在做这部电影时,因为不能在一起工作,他也很崩溃。是真的。就像你欣赏音乐或演唱的时候,你能够感受到身体语言,你可以感受到身旁那个人的能量,你明白有些事情是无法说谎的。这不仅仅是智力的过程,更像是直觉,一种感知力。在同一空间,你能真实体会到电影和音乐给人的感受,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当电影和剪辑快要完成的时候,我会邀请一些观众观看,和他们坐在一起,这个过程你能学到很多。你可以直接看到电影的感染力,你也能看到不足,你必须保持谦逊,虽然有时候自尊心会受伤,但你必须经历这个过程。这能让你学到很多,而这些是无法通过远程来感受的。
提问:但在视觉特效方面,远程工作的效果却还不错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是的。这一次很关键,我和大师级别的波林·格里伯特一起工作,我们有着相似的对事物的感知。特效的过程与剪辑不同。如果说剪辑更像一起玩音乐的话,特效则是一个对所看所见进行反馈的过程。观看、反馈、修改、再等一两周看到结果的过程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清晰的头脑,保持一定距离,有助于得到更自然的反馈。你需要专业的设备支持。目前为止,特效部分进行得非常好。
在《沙丘》项目中,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特效团队,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鼓舞着我。我和特效团队几乎每天都开会,通过网络进行一小时的会议。当我在家里看到他们分享过来的画面,支撑着我度过疫情阶段,眼见着特效慢慢完成,工作慢慢完善。我们的团队其实分布在世界各地。特效团队成员有的在温哥华、洛杉矶、蒙特利尔,也有的在欧洲、亚洲,世界各地都有。所有人在家的努力成果,最后汇集到我这里。

提问:我们来细聊一下《沙丘》的世界。这是对弗兰克·赫伯特1965年小说的改编。你是如何执导这部电影?又如何看待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的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初读《沙丘》这部小说,那时我大概13、14岁的时候。坦白来说,我是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这本书的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封面的时候,我还是一个深爱读书的青年。我喜欢阅读,并从中寻找各种新鲜事物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,我开始展露出对科学的擅长,我开始对科幻小说越来越好奇,越来越讶异和惊叹,特别是《星球大战》。你知道,1977年《星球大战》的出现让我一下子成了它的目标观众。《星球大战》有很多元素取自《沙丘》。众所周知,乔治·卢卡斯也是《沙丘》的书迷,所以能轻松地从中汲取灵感,吸取一些书中的元素,一些神话体系,一些世界观架构和故事推动力。
《沙丘》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小说。第一次见它时就有这种感觉。我看到这本漂亮的书,封面上有一个蓝眼睛的男人。我现在还保留着那本书,仍然记得当时被它的封面所惊艳。我还记得我翻看了书的背面,它的确吸引了我,我深深沉浸其中,读完了这系列的全部小说。这是一个传奇,一共几本书,用某种方式描绘了世界的复杂性,美丽又丰富的文化。一个男孩离开家乡,不得不在一个新的现实中适应,在新的文化中生存,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去拥抱新的文化,在那个环境里生存。这让当时的我深受感动,我那时也是一个年轻男孩。同时我也认为这本书探讨了、经济,我们如何解决自然资源问题,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破坏。作为一个孩子,对我来说,这是一本复杂又充满力量的小说。通过一个强大又简单的普世故事,同时探讨复杂的议题。老实讲,它成了我那时最喜欢的书。我深爱着它,并且在我以后的生命中也将会持续这种热爱,它就像一个古老的梦。我曾对自己说,有一天我要把它搬上银幕。
我记得我很激动,当大卫·林奇将它改编成电影的时候,我非常激动,我一直期待着看到它。事实上,当我看到电影中有很多我深爱的元素后,我就觉得大卫·林奇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,他是一位大师,我非常敬重他。但同时他的改编中也有另一些让我感到疏离的部分。那是他眼中《沙丘》的样子。我明白了不止一个《沙丘》的含义。有一种情绪总是触动着我,我对自己说:“也许是将来的某一天吧,我会拍《沙丘》”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拍电影,但主要是加拿大的一些低成本电影,科幻片对我来说遥不可及。来到好莱坞之后,我开始拍摄更高成本的好莱坞。人们不停地问我:“你的终极梦想是拍什么样的电影?”,或者“你想要做什么?”,我一直说我想拍科幻片,我想拍《沙丘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传奇影业的玛丽·帕伦特和凯尔·柏伊特拿到了版权。他们一拿到版权给我打了电话,这可能是我开过最短的一次会议。我们只是说了句:“我们要一起拍《沙丘》吗?”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从一开始,我们就对《沙丘》原著以及这个故事该如何被讲述,有着同样的感触。在项目中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合作。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目前为止经历过的最大挑战。

《沙丘》剧照
提问:既然《沙丘》的影响力如此巨大,那么它对你之前的电影也有过什么影响吗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我会说,它加强了我对无尽沙漠的渴望。对于保罗来说,关于沙漠,那些空旷景象的冲击,寂寞的冲击,都成为了他内化的、潜意识的旅程。这意味着当人物走向沙漠更深处时,我们也走到了他内心更深处。这是我从书中感受到的,自然景观对人类灵魂的影响。我在以前的电影创作中也有所尝试。我最初的影片,一男一女在沙漠中爱上了对方。更准确地说,是一段发生在沙漠中以失败告终的爱情。这不是巧合,而是我想要探究景观如何影响人类,自然如何唤醒内在情感。
你看我早期在约旦拍摄的电影《焦土之城》中也出现了沙丘。这部电影改编自瓦吉·穆阿瓦德的作品,我在其中展现了一部分沙漠,是在约旦取景拍摄的。我记得是因为我在约旦游走观察——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陌生的中东国家,这个不存在的国家却代表了黎巴嫩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部分。我经常说,我走遍了约旦,探索了约旦沙漠的每个角落。我记得我对自己说,这对《焦土之城》来说不够适合,但对《沙丘》来说却显现着近乎疯狂的美。如果我要拍《沙丘》的话,一定会回来这里取景。我确实这样做了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《沙丘》已经存在于我的作品中好久了。
提问: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演员的选择和拍戏时的合作。你是如何挑选演员的?更看重演员的哪些特质?可以结合《沙丘》这部电影,也可以谈论一下你的其他电影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选择演员非常非常困难,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过程,但同时又是一个让你兴奋的时刻,但同时又很紧张。你需要一个演员化身成这个角色,赋予角色语言和生命。更重要的是,你需要找到你的缪斯,你需要找到能激发你灵感的人,能激发你创造力的人,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。就《沙丘》而言,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但非常有趣。
让我非常开心的是,我大多数的“第一选择”的演员都会被项目本身的魅力吸引,并答应参与这个项目。对于《沙丘》这部传奇一般的经典来说,说服人们一起加入并不是难事。刚开始提莫西·查拉梅就是我的第一选择,我心中的保罗·厄崔迪就是提莫西。和提莫西见面后我们立刻达成共识要一起合作。说服提莫西并不难,选择提莫西有几个理由:首先他是一个现象级的演员,他极具深度,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。保罗·厄崔迪年轻的身体中住着老练的灵魂,提莫西也是如此,看起来比他的真实年龄还要年轻。有时我看着镜头中的他 ,感觉他只有15岁,但实际上他大概有23岁左右了,这真的很令人惊讶。他深邃而饱经沉淀的眼神也起到了很大帮助。而且他已有超越年纪的成熟,能够制造这种年龄的反差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他的一些特质也会让我想起过去经典时代的好莱坞电影明星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电影明星,疯狂散发着个人魅力。你将镜头对准提莫西,会感受到魅力爆发的瞬间,就像摄像机突然被他吸引住一样,非常有魅力。这也是保罗需要具备的特质。保罗是一个需要在某个时刻领导和激励别人的年轻人,成为一个领袖,他需要这种魅力。而提莫西有这种魅力,从某种意义上讲,他就像一个摇滚巨星一样。我需要那种魅力,我需要他可以刻画出保罗不同层次的性格。
现在我可以将(《沙丘》)所有演员都细数一遍,但这可能要花上3个小时,因为这个项目中让我有机会和一群现象级的演员们一起工作,而每一位的选择都有其特定的原因。例如我选择杰森·莫玛是因为他对待冒险放荡不羁的态度、他在银幕上的优雅、镜头中不可思议的笑容,都散发着致命的魅力。他打斗的时候像是一个芭蕾舞者。作为银河系最好的战士之一,需要呈现一种骑士般的高贵、勇猛,同时又不失幽默,他是这个英雄的不二人选。同时我也有幸和乔什·布洛林一起合作。他是我之前就合作过的演员,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细数每位演员,这个话题能聊很久。我曾经和乔什·布洛林合作过,我一直想和他再度合作,因为他是我喜爱的演员,也是我喜爱的诗人。他在片中扮演哥尼·哈莱克,一个诗人、战士,有时略显颓废。当乔什出现在银幕上时,你会爱上他的角色。尽管他的角色有时不修边幅,这正是我需要的。作为保罗最好的朋友,他也需要这种气质。我希望能和乔什·布洛林一直保持合作,他真的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演员。我也很早就想和奥斯卡·伊萨克一起工作了。奥斯卡完全符合小说对雷托公爵的描述。他也是当今最的男演员之一,我一直在寻找与他合作的机会,最后他同意饰演公爵。还有斯蒂芬·亨德森,他的角色可以用“人类计算机”来形容。《沙丘》世界中不再出现计算机,人类决定把机器弃之一旁,使用大脑工作。其实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斯蒂芬正好是我想寻找的,一个眼睛里充满智慧,同时又看起来像泰迪熊的演员。我想要观众在看到斯蒂芬的瞬间,就自发地爱上他,想要拥抱他。在确定完提莫西参演之后,我们紧接着邀请到的是丽贝卡·弗格森。选择她的原因也很多,她是一名伟大的艺术家。我认为她能胜任杰西卡夫人这个复杂的角色,这个人物层次很丰富。还有夏洛特·兰普林,这位长久以来我渴望合作的女演员,对我来说是一个传奇,我喜欢她有25年了。斯特兰·斯卡斯加德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。我的老朋友大卫·达斯玛奇连,我希望我所有电影都有他的身影,因为我很享受和他一起创造人物的时刻。同样还有戴夫·巴蒂斯塔,我和戴夫在《银翼杀手2049》中有过合作,没有比他更适合演“野兽拉班”的人了。戴夫非常可爱,但他长得很凶很吓人,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,他是一个能感动我的演员。对了,还有震·张,中文里应该叫“张震”。我从90年代王家卫的电影就开始关注他,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演员之一。我在很多电影里看到过他,被他自然的表演深深打动,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之一。

演员张震——《沙丘》
提问:和这些演员们一起拍摄,你感觉怎么样,或者说你和演员是怎么合作的?你如何给意见、如何给他们导戏?你在片场一般如何指导演员们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我认为有两件事非常重要。首先是准备要足。对我来说,所有的智识上的工作都要在拍摄之前完成。我喜欢在一个完美场景下工作。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晰,对话也好,场景也好,所有智识层面的讨论,都要在准备阶段完成。所以在前期的时候,这时候我会和演员们沟通,和他们聊角色和影片情节逻辑,及时调整,我不怕做出调整。如果某位演员对于影片对白有更好的想法,因为有时候对白容易写得过满,编剧在撰写剧本时是想从文字到大银幕的过程,但当你看到演员的眼神,就知道可能有另一个表达方式。这在我和演员们的沟通中时有发生。当这部分智识工作完成之后,我在片场就更专注于场景的视觉化,专注于情感,引导演员经历情感变化。这个指导过程不要太理性化,因为我很注重情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最终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人的变化过程,以及那个场景对人的影响。大部分时候,在我个人看来,当你在那个场景里时,想法就会随之出现。因为它本来就被安置在那个场景里。
我的工作方式是,尽量多给演员空间。希望是如此。首先我会确认,最大程度在真实的场景里进行拍摄,而非特效场景里。我相信那影响着演员的创作过程。演员们能知道,这里有一扇门,这里有沙发、房间的色彩布局,这里有灯光、也有植物,这些都会激发创意和想象。它能在演员内心产生张力,制造压力,也可能是其反面——自由。而我作为导演,最重要的是观察与聆听。开始阶段,我需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,聆听他们,看他们从直觉里带来的东西。有时候他们也会有不太好的创意,我会忽略这些。有时他们的创意比我的要好,我要及时地去倾听。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平衡。有些演员的直觉比其他人要好,这些都很自然。这是灵感,而不是科学,需要你有敏锐的感知力。一个好导演同时也是一个好的倾听者。我导演的经历越多,就越发觉得,开始阶段,导演需要允许有一定自由的限度,让一些诗意的想法有机会进来。我对此始终坚信,我说的不是即兴创作,而是给创作者空间。
提问:在你成为导演的职业道路上,有没有对你影响颇深的电影人?他们的电影作品是否也影响了你自己的风格、定位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有很多电影人对我的影响颇深,他们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中一位,直到今天依旧对我非常重要的,无疑是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。我来自一个小镇,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大部分是美国电影。而有一类电影和其他电影截然不同,这类优秀电影都和一个名字有关,带着这个名字的电影就意味着质量保证。慢慢大家就意识到这一点。那个人做着一种工作,那个工作就是导演。而他的名字就是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。后来我开始看一些幕后花絮,开始明白这个工作的重要和意义。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 ,我最喜欢之一是《第三类接触》。而电影的主演弗朗索瓦·特吕弗是一名法国导演,所以这部外星人电影也让我发现了“法国新浪潮”。弗朗索瓦·特吕弗的作品中有对人类之间的爱的描述,他的描述如此深刻。我非常喜欢他深具同情心。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无疑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导演之一,他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导演。他创造了无数经典场景,与演员们一同完成调度,摄影技巧同样无与伦比,直到今天我也时常会重温他的作品,非常令人钦佩。在弗朗索瓦·特吕弗之后,我又知道了戈达尔。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智慧、乐趣和激励人的力量,激励观众做一个发声者。我当时是个自大的年轻人,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套很管用。
就这样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导演,斯坦利·库布里克也是对我影响非常深厚的导演。毋庸置疑,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演之一。在我探索电影的过程中,如果说到在精确与纯粹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实现平衡,库布里克达到了让人难以企及的境地。还有英格玛·伯格曼,对我产生了强烈的美学冲击,他深切地碰触人类的灵魂,到达人类意识的最深处,诚实地展现人性的真实。还有很多导演也对我产生深刻影响。接下来必须要说雷德利·斯科特。《银翼杀手》给我的美学冲击很大。在法语中我们称其为“视觉艺术家”(plasticien)。他能够建立起一个自己的视觉世界。还有无数当代导演是我非常崇拜的。先不提其他的法国导演,比如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:雅克·欧迪亚,还有欧格斯·兰斯莫斯。克里斯托弗·诺兰在我心中也是无可超越的存在。绝大多数导演做不到的事情,他却可以。在操作巨大体量的项目的同时,还能保持自己的个人风格。我可以说是诺兰的头号粉丝了。在众多导演中还有一位,是每当我拿起摄影机就会想到的。实际上是两位:皮埃尔·佩罗和米歇尔·布洛尔特,两位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导演。他们在六七十年代拍摄的纪录片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和他们的作品没什么关联性。确实我们的作品很不相似。但时至今日我和他们一样,在自然面前感受谦卑,愿意去拥抱自然,并且从中汲取诗意。他们的影片中有这样一种情感,那是我至今仍在努力保持的情感。即使我如今在好莱坞工作,我仍感觉两位艺术大师离我很近。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我现在说的,因为他们不喜欢好莱坞,他们讨厌好莱坞,而且我不觉得他们会喜欢我的电影,但我深深敬仰二位,他们对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我想再补充一下,很多人都会问我哪些电影人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?我总是忘记真正的答案,那就是摄影大师们。在这里我想提两位摄影师。第一位是彼时很年轻的安德烈·图尔平。我最开始与他合作时,他还是一位年轻的摄影师。他捕捉真实的精准度极高。当然还有罗杰·迪金斯。当聊到作为一名导演最喜爱的电影人时,一定要提到迪金斯。他是位艺术家,以对光影的掌控闻名。但对我来说却不止如此,他确实擅长利用光影进行摄影,但在叙事方面他也非常了不起。我们一起合作拍摄了三部电影,我能在我们的合作中收获自我陶醉的愉悦。我就是很爱他,他的每一个镜头对我来说都是一堂电影课,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莫名相似。我用了“莫名”这个词,因为对我来说他是个摄影大师,甚至是摄影之神。就算我们已经是亲密的朋友,我还是对他怀有崇拜之情。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相近,因此当我们一起合作时一切都得心应手,无论是拍摄镜头还是布光等等。因为和大师一起工作,我还有一种在学校上课学习的愉快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想再和他合作一次的原因。关于电影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,与罗杰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荣幸之至。

维伦纽瓦与迪金斯在片场
提问:实际上迪金斯曾经说,您的电影是那种——在孩童时代促使他想进入电影行业的作品。两位的关系似乎对你们彼此都有滋养的作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跨越不同的作品,这种合作有什么变化吗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当我和迪金斯合作第一部长片时,我不得不遏制自己作为他粉丝的那一面,而要接受自己作为导演,需要给他提供指示的事实。刚开始的几天,我感到很不自在,也很尴尬。我在生活中通常不会轻易地钦佩某人,但总有一些导演或电影人,在他们面前我会非常羞涩。面对迪金斯,我的钦佩更加难以言表。在合作完第一部影片后,我们成为了亲密的好朋友,之后的合作也轻松了许多。罗杰·迪金斯对他人和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,他必须确保每一个镜头都无可挑剔,于是压力也随之而来,有时他会因为压力而稍显急躁。我曾对他在片场的脾气变化印象深刻,不过现在我已经完全习惯,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舒服。《银翼杀手2049》让我们的合作更加深入,我们一起探讨该用什么样的电影语言呈现。当时时间紧迫,我无法独自完成,便邀请迪金斯一起帮我制作整部影片的故事板,那也是迄今为止我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时刻。我和迪金斯,还有故事板艺术家以及詹姆斯一起坐在酒店房间里制作故事板。就像是和别人一起做梦一样,能够与他合作是我的荣幸,随着合作进行得更多、更深,我们越来越习惯听取对方的意见。很多时候我们无需多言,只需看着对方,通过直觉就能了解彼此的想法。这是一种很纯粹的情谊。
提问:还记得对于一部想拍的电影,你脑海中第一次出现它画面的时候吗?能否描绘一部电影在你脑海中诞生的过程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那么我就跟我的中国朋友们聊一聊我以前从未透露过的秘密吧,这件事说来有几分尴尬。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在脑海里导演电影了,这是我应对恐惧和焦虑的办法。因为小时候对世界感到害怕,每当我要睡觉的时候,唯一能够睡着的方法,就是在脑海中设计一个又一个故事,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世界。一晚一晚的故事就像电影的情节,帮我对抗焦虑,也让我与这个世界真正建立起联系。我从童年起就开始写作,一开始我以为我会成为作家,但我可能天赋不足。当我尝试导演的工作之后,就越来越痴迷这种通过摄影机讲故事的方式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摄影机,但好在我有个朋友擅长画画,我们配合得不错,我来讲故事、他来画,创造我们自己的世界。早期的我通过这种方式,试着去理解周围的世界,有时候是逃离。这可能就是我开始拍电影的契机。抱歉我忘了说,我和我的朋友尼古拉,在我们十二三岁的时候,就开始为《沙丘》制作故事板了。那时我读这本书读得津津有味,便一起开始制作。我现在还有很多当时画的保罗·厄崔迪,还有沙虫。可以说当我还是孩子时,就开始梦想着将《沙丘》做成电影了。
提问:就像我刚刚说的,你很擅长在电影中利用观众对不确定性的心理,制造悬念。能否谈谈为了实现这种效果,通常采取的视听手段?例如:调色、美术、声音、剪辑等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这是关于制造紧张感的问题。每当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时,我通常会回答:这经常是凭着直觉实现的。这样的答案有点无聊,所以这次我会尽量回答得更详尽一些。制造紧张感的最重要元素之一,是让银幕里、影像里的东西具有真实感,从而使观众从潜意识的角度,能与之建立联系。可以是光,可以是植物,也可以是让这个镜头像梦境一样的东西,只要其中存在真实性。用光,就是电影制造真实感的强有力的工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要尽可能呈现多的……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喜爱罗杰·迪金斯的摄影。他的摄影理念就是把镜头里的东西拍得越自然越好。这样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信号,“你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真实的”。
然后你需要引导观众,让他们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看不到的,例如他们的所在,或者恐惧的所在。这时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展现它,给出一些暗示、声音,或者镜头运动产生的压力感,来预示某些事情将会发生、或者不会发生。然后就像炉子上的锅子,你开锅、等待水的沸腾,过了一段时间水会变得足够热,马上要沸腾了,你必须在这里切掉,这是紧张感达到顶峰的时刻。对我来说,一切都要从与自然和时间的关系着手,通过不在场的事物营造紧张感,这是靠留白制造紧张感的诗意所在。目前为止,表达紧张最佳的音乐,永远都是寂静。当你能够通过留白和寂静表现紧张感时,其效果会是很震撼的。

《沙丘》剧照
提问:在您1998年拍摄的长片作《8月32日》结尾处,主人公从魁北克飞往美国。今天看来,似乎也映射了您的导演生涯,您也是最先在魁北克,而后到美国继续拍电影。在这过程中,您拍电影的方式和态度是否发生过明显变化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确实有变化。在一开始的时候,我更痴迷于镜头运动,我有强烈的掌控欲。我在拍第一部电影时非常傲慢,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,去创造一种身份标志。拍了两部电影后,我意识到我失败了。我决定换一种方式看待事物,试着不去证明“我”的存在,换一种方式去表达,努力更谦逊地处理我的主题。由我去服务故事,而不是故事来服务我。我将自我意识摆正,因为热爱电影而去拍摄电影,而不是为了证明我存在,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改变。我还想说的是,我与演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和演员沟通的时候会有点不知所措,很多导演都有类似经历,觉得演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“物种”,这种感觉很正常。但我和演员合作得越多,就越感到舒服自在。我越来越成为一名好导演,去倾听演员的想法,并且更好得掌控工作,拥抱那些自己还没有答案的想法。我现在做得还不错,即使不知道正确答案,也能很自如。作为导演,常常要回答上百个问题。我现在觉得,如果用法语来表达是“自我原谅”,对自己友善,静待花开,即使有500个人等着你,即使太阳就快落山,火正在燃烧,你也要耐心等着花开。花终将绽放,我们必须保持耐心。因此你必须离开焦虑圈,然后再回归创作。这些是我多年来学到的东西,当然我还学到了很多技术上的东西。
提问:《囚徒》和《边境杀手》是您早期的美国电影作品,此后您便投身科幻片,从《降临》、《银翼杀手2049》到《沙丘》。很多人认为这是非常巨大的转变。但实际上您常说,这和您年轻时的热情是一脉相承的。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是的。经常有人问我,你现在怎么开始拍科幻片了?你为什么进入这个领域?但我想说,我不是“去到”那个领域,而是“重返”那个领域。我爱科幻,我从一开始就梦想着拍科幻片。我认为要想拍出优秀的科幻片,必须掌握很多要素。对那时的我来说,可能是一种非常困难的类型。所以为了拍好科幻片,我必须在拍摄其他题材的过程中改进和优化拍电影的技艺,在现实中耕耘,才能离梦想更近。我现在能够执导科幻片的另一个原因是:我的预算变多了,也有了足够的经验指导,能够指导更大的工作团队,掌控更复杂庞大的视效。我不可能把《沙丘》作为我的作,如果那么做的话,我现在已经玩儿完了。
提问:您之前提到过,对您而言重要的是这些科幻场景要在真实环境中拍摄,而不是绿幕前。当今技术发展迅速,您如何看待自己与视效的关系呢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现在电脑是非常强大的工具,能制造很宏大的场景,甚至创造一个世界。当然这是我们之前无法做到的。但在过去,导演和视觉艺术家都是大师,他们能运用非常复杂的技术来创造事物。如今利用电脑,会比之前容易一万倍。因此,可以很肯定,我们现在有更大的灵活性。但在我个人看来,存在的危险是,归根结底,电影的灵魂是语言和演员,要让电影拍摄得到最好效果,你需要去激发演员。而要激发演员,我认为大量的“真实”元素很重要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有时不得不在虚拟环境里进行拍摄,对我来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最终真实的效果,是很困难的。因为我不认为创意能够凭空突然冒出来。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,我会对一张被照亮的桌子有感觉,我对房间里椅子的位置有感觉,我对演员是不是以某种特定姿势和角度朝着一扇窗户走过去有感觉。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有一扇窗户,窗外也得有东西,这就像你在为创造力和想象力储备食粮。包括站在绿幕前也一样,你需要在场感。作为一个导演我永远会为在拍摄中有更多真实而努力,拍《沙丘》的时候也尽可能在真实的场景中拍摄。我们搭建了很多非常宏大的场景,我们需要借助这些来思考。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世界,创造一个新的星球,那我们就需要用储备“好的粮食”去创造,我认为这些真实的环境布景很有帮助。当然电脑可以帮助我们完善,使这个世界看上去更大,让东西飞起来,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完成得更完美。但是围绕演员的核心元素则需要是真实的。
提问:作为一个导演,同时也是影迷,在您看来,是什么构成了一部好电影?换句话说,你认为一部好电影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什么?
丹尼斯·维伦纽瓦:诗意。我认为,归根结底,观众为什么要去看电影?是因为要在影像的诗意中找到感动。当你与别人交谈时,偶尔提到某部电影的名字,你的脑海里会自发地出现一些场景。那些因为某种原因深深印刻下来的场景,会触动你的内心深处,它们有着深刻的含义。这些含义是制作团队在拍摄和打光时就精心策划的。这些设计元素创造了一种无形的含义,它不可言喻、不可见,这就是诗意,这就是电影诗意的美。作为一名电影人,你要在电影中创造尽可能多的这样的场景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