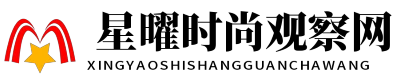电影《脐带》是青年导演乔思雪执导的首部长片。影片主人公阿鲁斯是一位音乐人,为陪伴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,二人返回草原,寻找记忆深处真正的“家”。表面看来,影片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背景的阿兹海默症故事,但其本质在于回返生命本源,而这种回返是通过具有拓扑学意义的脐带完成的。
三次回返
影片的回返一共有三次。第一次是阿鲁斯接到母亲的电话,回到家乡看望生病的母亲。在第一次的回返中,阿鲁斯并没有回到真正的草原,而是从大都市回到尚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,是从中心返回边缘。此时,回返仅仅意味着空间的转移和景观的变化。返乡的阿鲁斯坐在封闭的出租车内,冷眼旁观着家乡的道路、楼房与人群。母亲随哥嫂一家居住在城市的楼房里,困居于斗室的她在墙上画满了蒙古包、牛羊马匹,以及一棵一半生一半死的树。被疾病剥夺理性的母亲努力突破楼房的束缚,用绘画、吵闹等身体行为进行对抗,将自己的意识对焦于潜在的记忆,主动地寻找一种生命深处的景观,还原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草原生活。这种还原行为在后两次回返中得到了实现。
第二次回返,是阿鲁斯带着母亲回到“老家”。这个家为生活展示了一种物理上的确凿证据:它是一座砖瓦结构的房屋,临水而建;屋内有家具和衣物,陈设着一家人的老照片;长久空置之后,缺少现代生活所必需的电。除此之外,在更广阔的草原空间和游牧民族的背景之下,这座房屋也意味着游牧的终结与定点而居的开始。对于阿鲁斯来说,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,是他所认为的家。但对母亲而言,她所不懈寻找并渴求回返的是一个更具原初的所在,她要回到儿时那个有父母的家,找到那棵一半生一半死的树。
于是便有了二人的第三次回返,阿鲁斯带着母亲深入草原。这次他们回到真正的草原,回到游牧的行动方式,回到本源意义上的家。影片中,回返到原初并不意味着全然抛却当下、抛却自我。相反,不论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阿鲁斯来说,回返是对于当下和自我的重新构建。母亲在回返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衰老与疾病的肉身束缚,旅程的终点是死亡,但死亡意味着新的自由;儿子在回返的过程中倾听草原的声音,发现生命的起点——起点是母亲,是草原,是镌刻在血液和灵魂中的游牧基因。而这个起点,被整个游牧集体、自然万物所共享。
作为“莫比乌斯环”的脐带
在科学领域,“莫比乌斯环”属于一种拓扑结构,被用来象征无限循环和永恒。“脐带”是电影的片名,也是电影中最重要的意象,但它并不单纯地具有母亲孕育儿子这一重意义,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个“莫比乌斯环”般流动的结构。
作为一种连系结构,脐带将母与子化为一体。当胎儿出生,脐带被剪断,之间的关系逐渐脱离生物性而被具化为生活和存在的关联。回到草原之后,阿鲁斯为了防止母亲走失,在两人的腰间系上绳子,母与子重新在物理意义上联结为一体,相伴着深入草原。不同的是,在婴孩时期,是母亲引领并庇护孩子长大,而当母亲年老患病,是儿子牵引、制约着母亲,成关系中的引领者与庇护者。脐带将连为一体,同时也提供了情感角色转变的通道,因而形成一个流动的“莫比乌斯环”,爱与被爱、需要与被需要、引领与被引领可以发生转换。
如果说脐带是一种将两个不同事物连为一体的连系结构,那么让母亲魂牵梦萦的生死树也可以视为联结天与地、生与死的脐带。树生长在天地之间,在物理空间中有一个确定的处所,与自然世界发生着物质交换,沟通天地,为万物提供荫蔽;这棵树一半行将枯死而另一半却茂盛苍郁,本身也是一个生与死的融汇点。母亲渴望回返到生死树,实质上是渴望回返到已经去世的父母身边,回返已经不复存在的家园。这个回返的过程与母亲自己的死亡过程是同步展开的。对草原人民来说,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与消亡,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,亡人不会消失,而是回返到草原深处的另一个时空中。因而作为脐带的树为我们揭示出一种宇宙意义上的流动性:在草原上,天与地、生与死、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隔阂,而是无穷无尽的联结与转化。
从回返到新生
影片用十分诗意的方式呈现母亲的死亡。悠扬的马头琴与歌声,伴随着飞扬的篝火,阿鲁斯终于剪断了绳子,母亲看见前来迎接自己的父母,走向草原深处,回到自己的所来之处,获得另一种形式的新生。阿鲁斯则独自启程,继续穿越草原。最终,他找到了那棵将生与死、天与地融汇起来的树。在三次回返的过程中,他也重新发现了母亲、故乡、草原、音乐的意义,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。
脐带的拓扑学意义不仅关乎情感,也关乎存在的方式与世界的意义:万物流转,死即是生,过去即是当下,起点即是终点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,母与子、生与死、过去与未来、传统与现代之间呈现为一种互联关系,血脉的连接、文化的承续、自然物质的转换都融汇在这个无限流动的结构中。这场行动,不仅使母亲和儿子完成了回返与新生,也意味着对草原民族与文化、自然与世界之起点的回返与叩问。